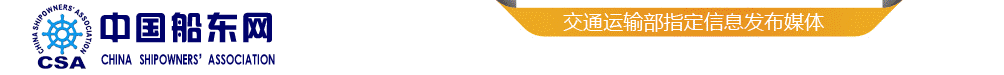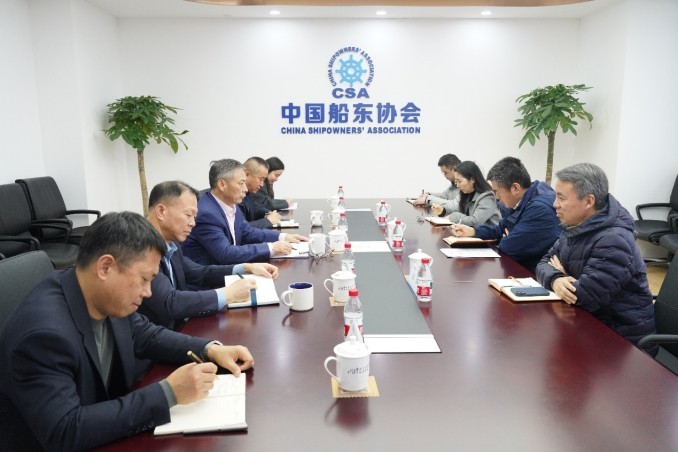英国上诉法院:“长赐”轮的船东和救助人未订立救助协议

航运人应该都清楚记得三年前霸占世界各大媒体头条的“长赐”(Ever Given)轮苏伊士运河搁浅事故。SMIT是世界知名的海上救助公司,其团队和其租来的两艘拖轮参与了重新浮起“长赐”轮的救助工作,为该船最终成功脱困作出了贡献。
SMIT和“长赐”轮船东随后签订了书面管辖协议,约定SMIT的救助费用索赔相关问题,将由英国法院专属管辖并适用英国法确定。在这份协议中,SMIT主张其提供的服务将使其有权根据《1989年救助公约》或英国普通法获得最高不超过获救船舶价值的救助报酬;船东则主张SMIT提供的不是《1989年救助公约》或英国普通法规定的救助服务,而是根据双方订立的有固定费率的协议提供的服务。
英国法中,当某人自愿(即没有任何事先存在的合同义务或其他义务)从海上危险中成功保全或协助保全了任何船舶、货物、运费或者其他公认的可被救助的标的时,该人就享有救助报酬请求权。在没有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确定救助报酬的情况下,救助人可主张的救助报酬数额不超过救助服务终止之日和终止地点所评估的获救财产的价值。如救助不成功,救助人无论付出多大的努力,都无权获得任何报酬;这就是“无效果-无报酬”(no cure-no pay)原则。
由于“长赐”轮最终成功获救并被送至安全地点,如果SMIT提供的服务是《1989年救助公约》或英国普通法规定的救助服务,则其有权主张的救助报酬的数额将有可能达到获救的“长赐”轮的价值。但是,如果SMIT是根据一份确定了其报酬数额的有约束力的协议提供服务,则其有权主张的报酬仅限于协议约定的数额。
2023年3月30日,英国高等法院判决,SMIT和船东之间未达成有约束力的救助协议,因此SMIT有权根据《1989年救助公约》请求救助报酬。船东上诉。一审判决的解读请见《【专栏】“长赐”轮的船东和救助人订立了有效的救助协议吗?》。
2024年3月19日,英国上诉法院二审驳回了船东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The Ever Given [2024] EWCA Civ 260)
双方当事人对适用于争议的法律均无异议:在判断双方当事人是否已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时,必须考虑双方当事人谈判的整个过程;即使双方当事人认为他们之间需要有一份正式的文件,其中可能包含一些没有商定的条款,但在这份文件之前,他们之间就有可能成立了有约束力的协议。双方当事人是否有意图建立有约束力的法律关系,必须通过客观评价他们的言行来确定。主张协议已经成立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证明责任。
有一些众所周知的措辞可以用来说明双方当事人的谈判尚未形成有约束力的协议,如“以签订合同书为准”(subject to contract),“以细节为准”(subject to details),但这些措辞的使用并没有决定性意义。一切都取决于双方在订约背景中的言行。

在判断SMIT和船东是否订立了有约束力的救助协议时,争议主要集中在2021年3月26日周五上午SMIT向船东发出的三份“最后通牒”(ultimatum)的理解上。在这三份“最后通牒”中,SMIT都表示,他们需要在荷兰时间当天中午12点之前和船东达成协议,否则将不得不采取强硬立场 ,停止提供服务以保护其利益。第三份“最后通牒”发出约一小时后,SMIT和船东就包括救助报酬的计算标准在内的几个方面达成了协议,但是在提供救助服务的范围、救助人注意义务的标准等重要问题上,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3月26日晚些时候,重新浮起“长赐”轮的努力失败,这意味着,救助工作需要更多拖轮 ,而船东对于SMIT的服务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在双方对救助报酬的计算标准达成一致意见后,SMIT斥巨资租用了两艘马力强劲的拖轮 ,以便更好助力“长赐”轮的重新起浮作业。
船东在上诉法院主张:这三份“最后通牒”是SMIT对船东要求其雇佣拖轮提供援助的回应。从该回应中可以看出,SMIT本不打算承担雇佣拖轮协助起浮作业的巨额费用,因为这些拖轮并不能立即抵达事故现场开始作业。如果在拖轮抵达前,“长赐”轮就已经被成功起浮,SMIT可能不能获得报酬。因此,SMIT有必要制定一份有约束力的协议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这也是SMIT在3月26日上午和船东交流的成果,即获得了一份有约束力的协议。如果有救助报酬计算标准的协议不具有约束力,这种协议就无法为SMIT提供任何获得报酬的保证。而且,在3月26日之后,双方沟通的基调就完全变了,SMIT再也没有发过“最后通牒”,原因正在于SMIT获得了继续提供服务并能确保获得报酬的保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种变化只能用双方当事人认为他们订立了有约束力的协议来解释。

SMIT在上诉法院的回应:第一,海难救助实践中,救助人通常会在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之前就开始提供救助服务 ,因此,SMIT租用拖轮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协议已经订立。第二 ,SMIT在早期和船东的交流中就倾向订立“无效果-无报酬”的LOF救助协议,而不是固定费率的商业救助协议。但是,船东更喜欢后者。所以,在3月24日和3月25日, SMIT已经两次向船东提供了涉及救助服务各方面的商业救助协议。这是一份完整的详细协议,没有留下任何有待进一步商定的内容。
因此,该案并非是当事人就主要条款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而没有讨论细节条款的情况。第三,双方交流时的预期是,一旦就报酬条款达成一致,其他事项就不会有争议,并将很快落实。一方面,双方本可以在3月 26日就订立协议,但实际上并未订立。另一方面,在上述预期下,没有必要在3月26日上午通过电子邮件来订立一份有约束力的临时协议。此外,SMIT完全没有签订一份临时协议的压力,相反,所有的压力都在船东身上,因为他们的船堵塞了运河 ,最近一次的起浮尝试没有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船东就越来越需要SMIT的协助,这样SMIT也就很有可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仍有权获得某种形式的救助报酬。第四,就报酬条款达成一致是合同谈判过程中的关键一步,但仅此而已。双方谈成该条款不意味着谈成有约束力的协议。第五,即使双方就报酬条款达成一致,但仍有一些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比如SMIT应提供哪些服务。
船东的主张所依据的所谓协议,并未规定SMIT有任何要履行的义务。事实上,服务的性质和报酬是密切相关的。SMIT最初准备提供的服务不包括为船舶减载或航道疏浚,因为这些服务对应了不同的报酬标准。最后,“最后通牒”并不像船东主张的那么重要 。SMIT寻求的是就所有事项达成一致,而没有暗示其会对仅就报酬条款达成一致而就其他事项完全不作规定的协议感兴趣。
上诉法院赞同SMIT的回应并认为,船东有义务证明当事人之间的交流明确了他们创设有约束力的法律关系的意图。但根据案件事实,他们之间的交流远未达到这一阶段。法院不认可“最后通牒”有船东主张的意义,因为三份“最后通牒”指向的都是SMIT提出的全部条款和条件。换言之,SMIT在任何阶段都没有明确表示或根本就没有表示其将满足于一份只涉及报酬条款的有约束力的协议。虽然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使用“以合同书为准”或“以细节为准”等措辞,但这对他们也并非必须。
上诉法院承认,签订协议的紧迫性在3月26日之后就不再明显,但主要是因为3月26日“长赐”轮起浮失败,SMIT就处于了有利的商业地位。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将“长赐”轮起浮的紧迫性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SMIT提供的服务实际上是实现该目标的唯一现实路径。如果船东不同意SMIT的条件,SMIT至少也能获得某种形式的报酬,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从SMIT的角度看,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订立协议的紧迫性,而且也使其租用的两艘拖轮实际使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3月26日之后订约的不紧迫性并不能说明当事人已经基于达成一致的报酬条款签订了有约束力的协议。
该案的两审判决展现了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当事人谈判救助协议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判决文本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英国法院如何分析当事人之间的通信往来以确定有约束力的协议是否成立。